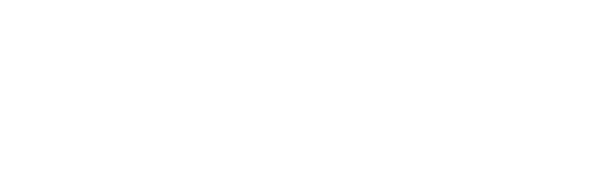作者:滕泰万博新经济研究所所长
全球感染新冠状病毒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超过了100万,其经济影响超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尽管长期全球经济可能不会陷入“大萧条”,但短期冲击的严重性已经是“短期萧条”。面对全球经济史无前例的“短暂萧条”,给予人民鱼的援助政策和给予人民鱼的经济刺激政策都非常重要。这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为了抵消疫情的外部影响,中国的救援和刺激规模应该不低于10万亿元。考虑到投资不再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新的基础设施不足以发挥主导作用,大都市地区受城市化放缓和各种制度约束,以铁公鸡为代表的旧基础设施基本饱和,消费已经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中小民营企业和服务业是业主的战场。 经济援助方向应主要是中小型私营企业、出口和传统制造业,而经济刺激方向应侧重于消费、服务业和新经济。
流行病传播的不确定性与全球经济的“短暂萧条”
这种新的冠状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和可变性,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远远超过了2003年的非典和过去100年的所有常见流行病。它的影响是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受疫情影响,企业不仅面临劳动力和供应链等供应冲击,还面临服务和替代消费品行业需求萎缩。一些企业还面临着现金流危机、债务危机甚至破产的风险。
从经济衰退的程度来看,短期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2008年。美国经济预计全年增长-2.8%,欧元区增长-4.5%,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至-10%。如果不考虑政府的新刺激计划,这些机构对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已经从年初的约6%下调至1-2%。
尽管短期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但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不是不可逆转的供过于求或需求不可逆转的供过于求。即使全球经济仍处于新技术产业化的起点,如5G、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新冠状病毒流行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是“大萧条”,而是“短暂的萧条”。
尽管疫情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延长衰退,但疫情的影响尚未损害经济运行机制或恶化经济结构。对于企业来说,虽然短期收益会大幅减少,利润会恶化,甚至资本流动性会变得困难,供应链也会中断,但只要影响持续时间短,大多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会受到损害。因此,必须迅速实施必要的救援和刺激政策,在大量企业倒闭之前必须采取充分的对冲措施,以减少经济衰退,帮助经济尽快复苏。
中国不会因为各国的刺激而缺席。
面对这一流行病和金融动荡的影响,尽管各国在初始阶段不同程度地错过了预防和控制的最佳时机,但它们的经济救援和刺激政策非常及时和深入。尤其是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将利率下调至零利率和负利率,提供了无限量的货币流动性,出台的经济救助计划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
其中,美联储两次将利率下调150个基点至零,推出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政策,购买公司债券和商业票据,并以2万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计划支持美国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居民,经济援助规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1%。除了两次降息之外,英国还向企业和员工提供了经济援助,2019年这一援助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6%左右。澳大利亚累计财政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0%;葛
尽管此次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欧美早两个月,但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行动相对较快,但在救援和刺激政策方面更为保守。尽管中小微型企业的部分税费已及时下调,并采取定向降级等措施增加少量流动性,但整体救助和刺激措施暂时落后于西方国家。上述谨慎决策具有长期的结构性考虑,也与国内批评刺激和批评释放等舆论环境有关。
一些中国学者不仅反对中国的经济刺激,而且对欧美出台的一系列救市和刺激政策评价不高。他们认为,即使上述政策出台,上述国家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仍将为负,股市可能会继续下跌。事实上,即使如此,上述国家的政策也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因为西方国家的套期保值政策原本是为了延缓经济衰退和减少损失。如果不及时出台上述政策,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将会更加严重。
至于中国的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可以主张很少或没有刺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供需冲击,经济不仅难以自行快速复苏,而且如果不及时采取稳定和刺激经济的措施,投资和消费的减少将形成负面的“乘数效应”。股市下跌和信贷紧缩形成了负面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以及一些企业倒闭可能引发的债务连锁反应.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按照旧的想法大喊“没有刺激”是有些鲁莽的。
其他学者认为,最困难的时刻尚未到来,因此降息和其他刺激政策的出台可能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事实上,在任何国家的经济低迷时期,像降息这样的政策都是反周期监管的必要和首选操作。在经济衰退开始时推出的任何政策工具都不能指望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宏观效果,但它可以增强信心、减少经济损失、降低企业成本,还可以悄悄地滋润万物。其他类似降息的政策工具不应等到最困难的时刻到来,然后拿出来赢得掌声。相反,应该尽快发布33,354个政策工具。然而,不应牺牲市场和经济稳定,也不应因为政策工具和政策资源被过分珍惜而牺牲企业和就业。
当然,对刺激政策的各种担忧和讨论不仅导致了相对谨慎的决策,而且一些观点有利于制定更有效的救助和刺激计划,特别是在如何平衡长期和短期问题以及如何平衡总量和结构方面。3月2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我们应该研究并提出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来应对短暂的全球萧条。我们相信,在应对短暂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救援和刺激行动中,中国不会孤立无援,它仍将在全球经济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援助和刺激的规模应不低于10万亿元,主要用于刺激消费。
面对前所未有的短暂经济衰退,无论是“给人以鱼”的经济刺激政策,还是“给人以鱼”的救助计划,都应该尽快出台。一旦错过了最好的机会,大量中小型微型企业和自营家庭将会倒闭。如果救援或刺激政策再次出台,将事半功倍。最新的城市调查显示,失业率从5.2%飙升至6.2%。虽然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和全面,但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严峻的失业形势。
考虑到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救援和刺激计划可能不一定侧重于具体的增长数字,而是确保合理的经济间隔和稳定的就业。此外,应充分考虑中国的经济增长
为了抵消疫情的影响,欧洲和美国的援助和刺激规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至20%。这不仅反映了各国对这一流行病影响的重视,也反映了它们自己对这一流行病影响的评估。这对中国的一揽子援助和刺激计划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考虑到一、二季度疫情造成的直接静态经济损失不低于5万亿元,对消费、投资和社会预期的动态负面影响更大,建议此次救市和刺激的总规模不低于10万亿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低于10%,占2009年财政金融扩张不超过15%。
从救市和刺激的方向来看,十多年前中国经济主要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所以当时的刺激计划主要是刺激投资和出口。如今,消费占中国经济增长的60%,服务业占53%。因此,这一轮的救助和刺激计划应考虑全面的救助和刺激,如消费者补贴、中小企业援助、新兴产业支持、智慧城市建设等。它不应该只关注新老基础设施投资。
就救济和刺激的分工而言,经济救济政策应该只帮助那些短期内受到重创但长期无效的部门,如出口部门和传统制造业,帮助它们在没有刺激的情况下度过难关,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对于消费、服务业和新经济,可以采取更多的支持和刺激措施来促进长期增长势头。
在选择投资项目时,新老基础设施项目都应根据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只要有需要,投资就可以现实地扩大。当然,最好选择类似智能城市的地区,这些地区投资乘数大,没有长期结构性问题。
在资金来源方面,除了将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5%,发行政府特别债券和扩大地方债券外,还可以从烟草、金融等行业拥有巨额现金流的国有企业获得较大比例的现金分红,这可以筹集2万亿元的非税收入。也可以将10%的国有股权转入社保基金,相应减少企业社保缴费2万亿元。还有可能将一些国有房地产资产证券化,将所有闲置的住房公积金返还给个人,甚至暂停部分一带一路项目资金以支持国内救援计划等。
第二,货币政策应摆脱舆论压力,尽快降息,并继续全面下调标准。
与欧洲和美国相比,尽管中国有很大的货币宽松和降息空间,但由于实践、理论和舆论的种种“负担”,如“货币是否流向实体经济”、“是否有洪水”,货币政策制定部门一直没有参与此次全球降息。事实上,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短期萧条”,货币政策无疑应该开展反周期调控的标准工作,果断而急剧地降低标准和利率。它不应与“理想”挂钩,如多年未实现的“资金流动微观机制改革”和“房地产调控”。
中国多年的实践证明,试图在短期内改变民营企业、中小微型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融资劣势是不现实的。分离和反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货币流动性也是不正确的。更荒谬的是,以“经济下滑过程中企业信贷需求疲软”为由,长期不放松货币政策,让实际的结构性货币紧缩导致经济下滑,进而降低企业信贷需求.然后得出结论,“在经济低迷时期,货币永远不需要放松”。
由于多年来实施结构性紧缩和探索“滴灌”的理想没有达到预期,我们应该面对现实:
由于疫情的早期防控最为严厉,中国经济将在第一季度遭受最严重的打击。但是,如果在短期防控基本完成后,中国仍不敢放松防控,中国经济不仅将受到重创,而且将遭受最长时间的打击。
截至4月5日,全国337个已确诊病例的城市中,有317个“清除”了现有确诊病例,占94%。大多数上述“零清除”城市,包括数以千计从未出现过疫情的中小城市,仍在以比实际需要高得多的标准实施防疫和控制。过度预防和控制对社会人口造成的心理阴影和压力严重影响了恢复生产和工作的整体效率,使经济很难重新启动。
如果我们要等到价格高得无法承受,大量企业倒闭,数千万人失业,社会心理平衡再次倾斜,那么我们就会逐步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恐怕许多经济伤害和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因此,对于疫情已“清除”数天的地区,除了保持防止境外输入的重点工作和戴口罩的防控措施外,社会成本低且不妨碍经济复苏,应尽快取消不必要的准入控制、不必要的异地人员隔离措施以及一些企业复工必须上报和出具的承诺书。
几十年的改革历史表明,中国许多行业的不合理行政管制政策大多是“短期供给约束和长期供给约束”的产物。这次为预防和控制疫情而形成的许多“供应限制”原本是临时措施,应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及时取消。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借此机会减少各行各业的各种行政规划方法对市场的干预,消除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砾石”,进一步放松对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让一切财富来源充分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