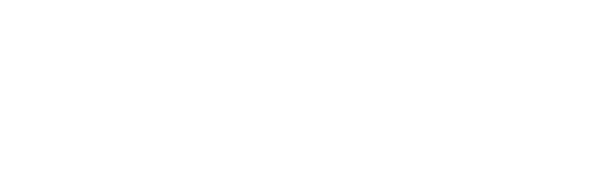在第一季度,银行“存款”是正常的,居民的担忧需要消除以刺激消费。
21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融集团研究所联合发布《疫情下中国家庭财富变动趋势--中国家庭财富指数调研报告(2020Q1)》。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50.2%)的家庭将在第一季度增加储蓄,减少消费,40.4%的家庭将保持现状基本不变,而只有9.4%的家庭将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调查结果基本正常,也符合一季度居民储蓄和消费的实际情况。受疫情影响,大多数家庭都是库存消费,而不是增量消费。所谓库存消费是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春节前购买的所有物品都是在春节期间使用的。虽然一些新的消费品也在增加,但大多数也是生活必需品。重点是食物和饮料。就玩耍、使用和居住而言,他们可以省钱,可以停下来就停下来,可以少用就少用,可以等就等,而不是在购买和消费中“冒险”。
也正因为如此,第一季度存在于银行和钱包中的资金现象将比前几年更加明显。消费的内在动机和热情被流行病严重抑制,并被流行病锁在笼子里。显然,对于消费来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无与伦比的现象。对于储蓄来说,这是正常的。用第一季度的储蓄和消费来衡量市场、消费者的消费热情以及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如果研究报告能够对第一季度受到抑制的消费者的消费动机和积极性以及流行后消费欲望的释放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从而对消费市场的未来趋势做出更多的预测和判断,该报告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为决策提供更有价值的依据。否则,只会“事后诸葛亮”,失去研究报告的意义和价值。
对于居民的消费来说,虽然内心的冲动很强烈,对“复仇”消费的欲望也很强烈,但是,也有很多担忧。首先是对流行病的担忧。换句话说,如果你乱花钱,比如聚会、娱乐、看电影和旅游,你有资格吗?这种流行病会影响这种消费模式吗?它会导致某些地方的疫情反弹吗?显然,这是消费者更关心的。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消费仍然会受到“报复”,这是很有潜力的。
第二,对就业和收入增长的担忧。由于疫情的影响,企业恢复工作和生产更加困难,尤其是中小企业。然而,大多数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大多在小型和微型企业工作。如果这些企业不能重返工作岗位,恢复生产,甚至关门,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影响将非常大,对消费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因此,消除居民对就业和收入增长的担忧是一项非常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第三,对物价上涨的担忧。可以肯定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太可能发生,但是价格的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货币发行扩张为价格上涨提供了条件。而这种状况,不仅来自国内货币因素,也来自全球货币流失的影响。尤其是最近几天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大幅下跌,为下一轮全球通胀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另一方面,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一些地区供应紧张,如猪肉价格、家禽价格、鱼类价格,甚至蔬菜价格。受疫情影响,可能存在“淡季”压力。在“淡季”阶段,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的价格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消费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第四,对房价变化的担忧。可以说,疫情过后,房地产市场应该会有一个相对较好的市场。然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居民仍然对房价的变化充满了担忧,既担心房价上涨,又担心房价下跌。因此,买还是不买是非常矛盾的。买,怕跌;不买,怕涨。然而,与前几年不同的是,当价格上涨时,他们只是抢购并购买。因此,如何稳定居民的住房消费预期也非常重要。
正因为如此,要激活消费,我们必须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从宏观上看,要做好防疫与激活消费的关系,不仅要保证居民消费不会受到疫情的持续压力,还要保证消费过程中不会出现新的疫情。与此同时,应该在政策方面给予居民更多的激励和引导,例如是否可以有更多的宏观政策来鼓励汽车和家用电器的消费。
在中观层面,要加大企业复工复产力度,加快供应链修复,加强产业链衔接。特别是中小微型企业的复工生产必须纳入地方政府的服务范围,而不是满足于规模以上企业的复工生产。否则,就业和收入增长将出现问题,消费将难以释放。
在微观层面,有必要加快启动刺激消费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一定需要自上而下,而应该更多地由地方当局决定。包括与企业合作推出刺激消费的政策,如汽车和家用电器,地方政府给企业一些优惠券支持消费,而企业提供更多优惠政策鼓励居民消费。住房消费也是如此。开发企业必须降价,地方政府必须坚决打击房地产投机,防止银行将资金转移到房地产市场。

总之,消费潜力很大。是否会有“报复性”消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释放居民的消费活力,形成有序、健康、可持续的消费,从而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